書名:歷史檔案館外傳:留一扇窗 Leave the Window Open
作者:薇多莉亞.舒瓦 Victoria Schwab
譯者:吉娃娃
【內容介紹】
《歷史檔案館2:惡夢》(The Unbound)的尾聲,麥肯琪和衛斯理兩人協同反將歐文一軍,歷史檔案館的危機解除後,回到現實世界。但因為打鬥的過程中,衛斯理傷口太多,所以必須送到醫院治療,與麥肯琪分開之前,衛斯理和麥肯琪說「留一扇窗」,就被救護車送走。
因此,外傳的時間是在《歷史檔案館2》結束後沒多久,將由衛斯理的視角,敘述處在醫院的感受與渴望,最後作者也會給於讀者們衛斯理始終不願開口的名字。
醫院充斥魔音穿腦的樂聲。
我的意思和字面上所呈現的根本是南轅北轍,這句話不是指進入電梯內因疲倦打瞌睡的人們、或是身處等候室的小康家庭用聊天、打鬧消磨難過的閒暇時刻(當然還有電視節目的人聲、翻閱雜誌時看見上面最新消息和火熱八卦激動不已的大叫,其實這些不算什麼噪音污染,因為發出聲響的人很快就會發現,在這所寂靜陪伴的醫院當中,聲音顯的特別突出,也就是人們會很快的意識,自己身處需要寧靜的醫院當中必須輕身細語)。不,我要說的是那些細微的嘶嘶聲、惱人的嗡嗡聲、刺耳的嘟嘟聲,其中不時摻雜其他病人需要幫助而按下的服務鈴聲、走廊上藥物車的輪子因為老舊發出的吱吱聲、遠處病患的咳嗽,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相互堆疊成了醫院獨特的配樂,醫院裡每個人當下的思維、過往的記憶也組成自身的單曲,獨一無二的不斷縈繞。它們刺激我、讓我在醫院療養時更難受,頭痛更加劇烈,也使我斷裂的肋骨不斷發出痛楚、等待復原的肩膀仍舊使不上力,若現正有個曲線圖,那麼我的狀況是一個下滑的模樣:從頂點的平靜,滑落到中點的難受,最後落至底谷般的恐慌,所以我沒辦法再花上任何一秒忍受待在那間醫院。
我從以前就很討厭醫院。
甚至不需要費盡心思來喜歡醫院,因為年幼時,別的小孩在外頭玩樂,而我則花時間在醫院照顧、探望生病的奶奶(她已經撒手人寰多年),如果這原因不夠強烈,那麼我爸在急診室工作,家中只要有人需要藥物治療——通常指的就我,沒有任何一人留心我的感受如何。我就是厭惡接觸醫院時耳聞的一切。雖然進入歷史檔案館不代表就能清靜些,但仍無法否認比醫院好上太多,任何人事物都好上幾百倍。
但我還是受困醫院,而我正站在診療室中,看著醫生把我的X光圖貼於左側燈板上。燈板的光線暗了下來,整片屏幕再次回歸漆黑,但是方才的圖像卻如鬼魅般揮之不去,已經深深的烙印我的腦海。感覺挺奇妙的,用這種由內而外的方式觀賞自己不曾見過的骨骼。讓人意識生命也可以如此脆弱。
記憶慢慢湧現,想像有份受傷清單,每當我因為打鬥得到的傷害都能在清單上打勾。肋骨斷裂,打勾;肩膀粉碎性骨折,打勾;內臟出血(沒什麼大礙),打勾。還有背後陳舊的傷疤、手部的毛裂狀骨折,身上到處都是傷口,唯一能怪罪的只有慶典爆炸時,因火焰燃燒而倒塌的布幔。可是卻沒有任何燒傷。因為當時我並不是真的受困於火場之中,我正在為自己的人生奮鬥,為麥肯琪努力奮戰著。
當然,我不能把真相說出口,如同我不能說背部的舊傷是來自我和歷史的戰鬥——拿著獵刀的老男人、牙齒如刀尖般銳利的男孩,還有歐文.克里斯.克拉克,所以住院時有位社會福利工作者前來探望我,確定我的傷痕不是來自我的家人。其實當下我忍不住想回答,我的家人就是造成心中傷痛的罪魁禍首,是的,我已經遍體鱗傷,因為老爸就像是我的肉中刺;我的繼母——不寒而慄——她是位既邪惡、貪得無饜又小氣吝嗇的賤貨,我張口慾言的差點說溜嘴,但最後我只是聳肩,說謊傷口是因為足球賽的關係,縱使老爸在我人生中扮演可憎的角色,但他因為缺席我的人生而留下的痛也比不上我打鬥時的損傷,而莉琪就如同方才想的既邪惡、貪得無饜又小氣吝嗇的賤貨。我想我可能不會恨她,前提是她得將挖金目標轉移到其他人身上。
然而我內心知曉社服人員、醫生不會百分之百相信我的足球傷疤論,但是達拉絲突然出現,然後說了一些話,他們原本欲求更多答案的嘴巴也隨之閉上,我想我欠達拉絲一份人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被醫院的獨有的配樂荼毒越久,我就越渴望有人能當我的代罪羔羊承受這一切。我想我氣壞了,因為我氣急敗壞的叫他們回家,而父親和莉琪也照做。甚至連和我討價還價的動作都沒有。因為他們的高貴打扮,猶如在控訴我將他們拉開某場重要的宴會——就像那句俗諺說的:「只要你夠富有和重要,無論何處都能成為你專屬的派對或晚宴。」整間病房就怎麼成了他們舉辨的筵席、一場世紀慶祝會。
所以我還待在這裡。獨自一人。在這裡我過的還可以、還不錯、沒什麼不好的,但事實並不然。
一旁的點滴將混濁的液體透過細微的管子,慢慢運輸到插在我手背的針頭,一點一滴的打入體內,讓我恢復元氣。我討厭針的程度不亞於醫院。可以猜想若是小麥知道,她一定會因為我怕針頭這件事取笑我,我想我應該會告訴她這件事,只為了看到她臉上的笑靨。我知道這樣讓我有點受虐的傾向,但我可以確定只有小麥的笑容,能夠撫慰我身心受創的自我。小麥身上也有許多瘀青,我想她應該也來陪我打點滴。
腦海開始想像某幅景象,在那想像中我可以看見我的背部,但我不再困在這間醫院的病床上。不,我將頭懶洋洋的躺在她的腿上,抬頭看著她微捲的赤褐色秀髮。這樣看去讓她的髮色顯得較深,我們愜意的坐在位於海德高中中庭的石頭庭院旁的階梯。沒有祝融、沒有爆炸、沒有歐文,只有我們。
只有麥肯琪,和她那少見卻令人難忘的笑容。
「說實話,小衛?」小麥在玩弄我的頭髮,她的手指輕撫我的額頭,撥開我的頭髮,讓她得以看見我的雙眼。「你確定沒有吃人的尖牙怪獸或是拿著刀的連環殺手躲在陰暗的角落嗎?」
我伸出手將垂在小麥臉旁的一縷髮絲撥到她的耳後。沒有打點滴的痕跡、沒有任何打鬥的傷疤。只有我的手放在她的肌膚上。
「嘿,聽著,」我說。「恐懼在這世上分成理性和非理性兩種,我們再確定一次妳的恐懼是哪種,會怕尖銳和鋒利的物品不是非理性的恐懼。」尤其是被刺傷後,對於那樣的恐懼會越來遲鈍,我只是想,但沒有說出口,因為我不該提及有關那天的任何話題。這樣做會更容易遺忘那天的經歷。
小麥給了我狐疑的神情。「你肯定是世上唯一一位有針頭恐懼症,但卻在身上穿了許多洞的人。」
「叫我恐懼大師。」我說。儘管事實是每次穿洞時我都拉凱許陪我,他是那種人人都知道的好朋友,因為他從來沒有讓我感覺陷入困境、那種父母都希望自己小孩結交的益友,但那只是表面,轉身就會發現他自在的靠著牆,悠閒的翻閱刺青目錄,好奇哪種刺青最能激怒他的父親。
這是虛幻/這是未來/這是假象,當麥肯琪彎下腰親吻我的額頭時,整個世界都因為她的親吻快速旋轉,速度快的讓我暈頭轉向。
天曉得點滴的內容物到底是什麼鬼,但它正慢慢蠶食我的意志,讓我慢慢脫離這陰暗光線的病房。感覺猶如自身夢境的邊界,但無法從睡眠中甦醒,縱使知道自己午夜夢迴,缺仍沒有餘力張開雙眼。
然後,恰似恐慌的寒顫從我指尖蔓延到我的神經,我的手機在一旁的桌上發出震動聲響。當我吃力的起身去拿手機時,胃部傳來陣陣疼痛抗議我的動作過大,但是這樣的痛楚值得。因為是小麥傳來的簡訊。
我照你說的留一扇窗了。
就這麼容易,漫遊的意志回來。我的胃痛暫緩,有某種東西身處在界縫中的感覺取代而之——若只看字面很怪,但保證不是像死人骨頭那種詭異事物,感謝上帝,但讓我有這番感受的事物處於界缝的深處,雖然我恨不得這該死的夜晚盡快結束,但我可不希望是用這種方式畫上句點。
我緊握病床旁的扶助桿,深深的吸口氣,做好準備迎接稍後痛心疾首的疼痛,長痛不如短痛,我吃力的坐起來,果然伴隨而來的劇痛使我頭昏眼花。當時我打鬥都沒有感覺到痛苦——我想是因為感覺麻痺的關係,才沒有感覺痛楚。其實回到校園後,也仍舊感覺不到一絲苦楚。真正讓我知道自己傷的多重時,是急診人員把我和小麥分開的當下,就像開啟某個不知名的按鈕,痛感如潮水般一波一波的朝我襲擊而來。
我在病床大口喘氣,稍加休憩,等到整間病房停止旋轉才開始進行下個動作。每次呼吸帶來的是更多傷痛,但我試著集中注意力在好的事物上,忽略這樣苦楚,提醒自己我會感覺劇痛難耐,是因為我是生者,還能感受到各種感觸。或許這就是烏雲背後的曙光,小衛。去感受生命力充滿全身。
換衣服讓先前感受的痛癢猶如小巫見大巫——更衣花費的時間讓痛楚劇烈增遞——我屏息以待,萬一護士在這節骨眼探房——就在我一隻腿穿進牛仔褲,努力取的身體平衡時,而另一隻腳在外頭等我穿進剩餘的褲管時——進來。
但幸虧沒有任何一人進來病房。
看著藉由盥洗室的全身鏡倒映的鏡像,我和鏡中的自己玩著大眼瞪小眼的遊戲。整體看去我還挺帥的。我的臉找到某種方式突顯我的眼妝,在我面色蒼白、多處瘀青的同時,我畫的眼影在眼皮上散開,猶如潑灑的影子般,而老爸認為醫生臉上的灰黑痕跡是因為拯救火災時所沾染到的灰燼,或者是因為跟著慶典上的學生們,一同用油彩的關係。會有這樣的想法,基於我認為老爸看到我化妝,比看到我躺在病床上還更困擾他。
雙手隨意的抓了塌陷的頭髮,然後試圖撫平因為我起身而充滿皺摺的床單,但是幾分鐘後,模樣看去比我平常躺的床鋪還糟,所以我放棄整理床鋪這偉大貼心的小動作。
「別太勉強自己,小衛。」內心突然聽見小麥可能會說的聲話,讓我不由得展開笑顏,然後笑容的代價就是讓休眠的疼痛再次甦醒。
現在我快要遲到。今晚的醫院不如往常,獨特的配樂沒有穿梭在走廊中,酷似有隻名為寂靜的怪獸吞噬所有惱人的聲音般,這也讓我溜出醫院的計畫更加容易成功。
我在我的牛仔褲的口袋中翻找鑰匙,但我不知道離醫院最近的夾縫界門位於何處,但又不能要求檔案館開啟通道,因為現在要我獵捕歷史根本是難如登天,所以最後我招了一台計程車,橫跨半座小鎮前去赴約。
想必這是我第一次高興看到科羅納多處處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思念猶如烏鴉棲息屋簷上的怪獸石像。我從來沒有告訴小麥,有時我會幫它們命名。州長、蘇格拉底、無頭海樂、麥艾爾坎等等名字。
到了目的地,付了車資後站在路邊,看著與我相距三層樓高的窗戶,那扇窗就是小麥房間的窗戶。其實確切來說,我盯著四樓窗口上方的窗戶,過去曾有一次,藉由這扇窗戶進入小麥的房間,但是我現在沒有把握今夜的身體狀況,是否能夠完成這次攀爬。
然後,奇蹟出現,想必是宇宙同情我的遭遇。我的電話再次震動顯示有未讀訊息。另一封來自小麥的簡訊。
我還有留扇門給你。
收起手機後我走進大廳,思考要不要走樓梯,但我決定駁回這決議,因為假如有人在二樓階梯發現心臟停止跳動的我,這樣想的話樓梯的抉擇就可以駁回,所以我決定走幾步痛的要死的步伐到電梯,讓電梯代替我的腳步引領我到三樓。
三樓就在不遠等著我。想要和她接吻的衝動不斷湧現。
我將耳朵輕輕靠在木製的門上,然後輕巧的轉動門把,動作溫柔讓我感覺恰似自己已經進入室內。公寓裡漆黑、幽暗,我試圖在黑暗中記起我穿越客廳,憑藉過去的感覺尋找前往小麥房間的方向。
進去後,月光從窗戶照射,賦予影子白日沒有的生命力。起初,我感覺她已經進入夢鄉,但是當我放輕腳步,慢慢從門邊離開時,她翻身。
「你來了。」小麥低語,因為我胸口的瘀傷,我感覺到她緊繃的語氣。
「因為這裡是我最想要來的地方,」我輕聲回覆,希望能舒緩她的緊張。「我希望進來時能更吸引妳的注意。從門進來不像從窗戶進入那麼戲劇化,而且……」話還沒說完,小麥已從床上下來,赤裸的雙腳沒有穿上一旁的布鞋,倆人之間的距離慢慢被她的步伐給吞噬,隨後她柔軟的雙唇就貼上我尚未說盡的唇片,當小麥擁抱我時,我的腦海中充斥著如雷聲般轟隆的聲響。
在小麥的觸碰下我大口喘氣,因為傷痛讓她退了一步,但是現正我最想做的就是親吻面前這女孩,所以我不顧身體因痛楚而發出的慘叫,再次將小麥拉向我並親吻她。小麥的手指和我的手指交纏,她牽著我的手引領我走到床邊,小麥躺回床上並在身旁留下剛好是衛斯理大小的位置,而我也緩慢的躺在專屬我的位置,這刻多麼完美,那些疼痛與哀傷都顯得滄海一粟、微不足道。
幾分鐘過去,我們倆人只是肩靠肩,十指緊扣彼此溫暖的手躺在床上,不是望著對方,而是盯著夜晚渲染的天花板。然後我看著她被月光照映的臉,把她的注意力從天花板轉向我,當小麥轉向我時,她的雙眼注意到我的手腕。
「你手上戴的是什麼東西?」她指的是醫院給我佩帶的手環。直到小麥提起,我都忘記自己方才還被醫院的聲音困擾的事,但她現在用那種好奇的眼神看著手環,彷彿這是世上最不可思議的事,感謝這如地獄般難看的塑膠手環。直覺立馬讓我知道小麥看見什麼,我能感覺血色慢慢從我恢復朝氣的面容退去,如果說感覺胃沉重到墜落在腳邊也不為過。
小麥瞇著眼看寫在手環上面的名字,印在上頭的是的全名註一,我想要用手指遮住我的教名註二,但已經為時已晚。我想再也無法不告訴她我的名字叫做什麼。我的教名。
坦普頓註三。
坦普頓.衛斯理.艾爾斯二世,這也是我第四十五條恨我父親的理由之一。原因相當簡單:什麼樣的白痴混蛋會取這種名字?
「小麥,」我想要開口阻止,仍舊是杯水車薪。她的笑逐顏開,不是那種平淡的咯咯笑聲,而是大笑,要立即遏止等於是不可能的事,我想要因為她的大笑發脾氣,但是老天,這笑聲是我這世上聽過最美妙的聲音,比方才親吻時聽見小麥腦海中的雷聲還悅耳。我可以去對抗噬血的怪物、跳下深不見底的懸崖,只為了聽她的笑聲,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要用盡所有的力量去壓制這笑聲,我用手摀住小麥大笑不已的嘴,縱使我想繼續聽下去,但還是必須狠下心。笑意沒有因此停止,反而讓她的胸口上下起伏。隨後小麥將手指輕撫我按壓她嘴上的手,然後一根一根輕柔的拉開。
「什麼也不要說!」我做出安靜的手勢,因為她獲得自由的嘴唇即將開口說出我之前誓死也不說的教名。「連嘴巴都不能張開!連想都不行!」
「好啦,不笑了……」小麥用蚊蚋的音量說:「坦普頓。」
聞畢,我發出痛苦的呻吟,但是這呻吟被她的吻打斷。我們不像剛才那麼渴望對方的唇,輕慢、溫柔,小心翼翼的不要接觸對方的傷口,我吞下撕裂般的苦楚,專心感覺麥肯琪.畢雪的親吻是多麼美妙。我正和麥肯琪.畢雪接吻。
「我很高興你告訴我你的教名。」她說,說完時還吸了口氣。
「但我沒有跟你說。」我指出話中的沒有成立的假象。
「這倒是,那我很高興我看見你的教名。」
「此話何說?」
「因為未來我們成為獵手搭檔時我不會笑,因為現在我會笑到肚子發疼,先把未來大笑的額度用光。」
我將視線移開。不是因為我不想聽這些話,我知道,內心也認同、也希望這這件事變成事實,但我怕這只是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妳是認真的?」我問,然後這次帶著戰戰兢兢的眼神和小麥四目相交。
小麥回看我,然後起身到我身邊,所以我不用轉頭就可以直視她的明眸。「當然。」她回答了我的問題。
若是有人對我說,我現在微笑的模樣像是腦弱我也不在乎。「讓我猜猜,妳應該沒有任何需要隱藏的難堪教名吧?不為人知的習慣?努力掩蓋的秘密?」
「只有一個。」
「是什麼?」
「我愛上一位名叫坦普頓的男孩。」
註一:外國人的全名是由教名(First Name)、中名(Middle Name)、姓(Last Name)組成。系列中,小衛只說自己的中名衛斯理和姓氏艾爾斯,對於教名則避口不談。
註二:教名(First Name)是出生時就會命名了。在西方社會裡,中名(Middle Name)算是第二個名字,不過通常大部分的人還是以教名為主要名字。中名不限定只能取一個名字,只是大部分的人慣用一個。國外,中名也很有可能採用父母名,有些男孩的全名跟父親一樣後面就會加上 Junior(年少、後輩之意)。有些外國人名字叫 J.J. 或 M.A.,那是教名跟中名的簡寫。
註三:坦普頓(Templeton)字義有有雙重性格。一方面開朗善良,另一方面又很難和别人相處。所以人們容易誤解。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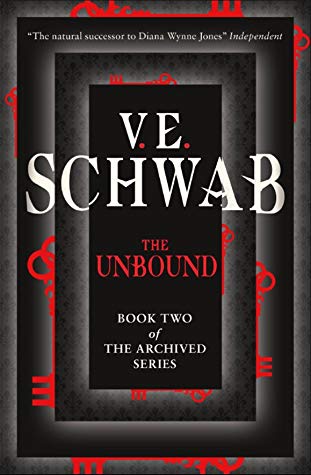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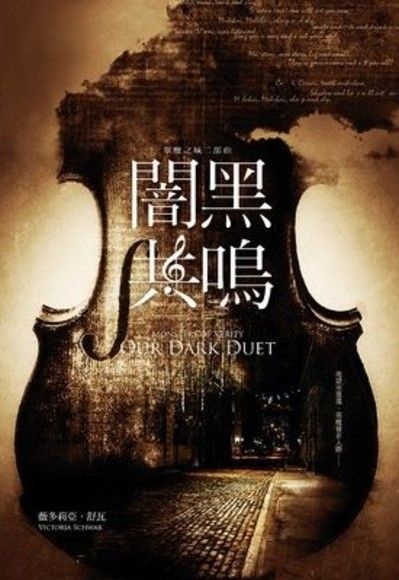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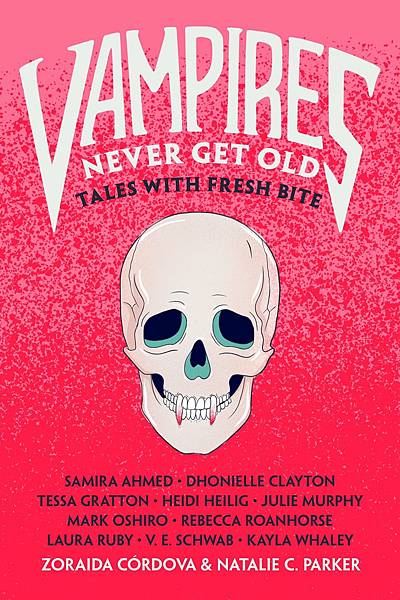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